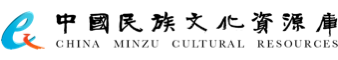
2013年12月,我曾对台湾高山族舞蹈文化有过一次10天的探访之旅。祖国宝岛湿润的空气、秀美的山川令人印象深刻。此外,那些高山族多彩的习俗、天籁的乐音、翩迁的舞姿更是让我难以忘怀。用心体味,我从台湾高山族舞蹈文化的发展历程得到昭示:传统与现代,或许可以从交锋化为和谐;我们或许也能够找到文化自觉的新路,而不至于迷失在“现代化”对传统遗产的消弭中……
台北·舞蹈文化的担当者——学人刘凤学
在舞蹈界,台湾新古典舞创始人刘凤学先生久负盛名,是我们此次行程首先要拜访的重量级学人。热情的刘先生不仅把见面地点约在了台北市家中,还特地邀请我们跟她共进午餐。
刘先生的家,几乎到处都是书,俨然一个小型图书馆。满头银发、目光炯炯的刘先生有些歉意地说:“看我这个房间差点连个座椅都放不下”。我在北京也去过许多大学者的家,但刘先生作为一位舞蹈学人,家中竟有如此巨量的藏书,着实令我有些震撼。
89岁高龄的刘先生出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县,满族人,长白师范学校毕业。而刘先生早期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创作,与我此行的调研有着密切关联。
上山,到高山族中间去
“大概念初中的时候,有个日本小男孩名叫高桥英一,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画了两棵椰子树,树下有几个台湾高山族阿美人,头饰很漂亮。他知道我很喜欢舞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向往台湾,像埋下了一颗种子。1949年,我随校迁到台湾。一来,就扎进高山族舞蹈里了。”
说起上个世纪中期的田野经历,刘先生记忆犹新:“曾经爬山一走就走一天,到了目的地后住一段时间再回来。那时候到山里去做研究需要申请,我先向当地县政府写一信,说明我要去参加高山族的丰年祭,哪一天去哪一天回,请招呼我一下。我自己找到山下的派出所,请他们找两个年轻的高山族接我上山,每次路上一走就是八九个小时。”
“当时,参加丰年祭的都是本族群的人,氛围原始朴实,也很清静。现在,社会传播工具太发达了,年轻人一听说哪里有丰年祭都涌进去了。热闹了,但好像失去了当初的气氛。”
刘先生的叙述,把我带进了那个田野场景。
从1954年到1979年,刘先生每年都到高山族住地实地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保存相关文化资源,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创作。谈到阿美人的甩发舞、布农人的八部合唱、赛夏人的矮灵祭等,刘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她曾对阿美、排湾、邹、赛夏、布农、卑南、雅美等九个族群的舞蹈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并创编了以高山族舞蹈元素为基础的舞蹈作品,如《云豹之乡》、《沉默的雏鹰》等,撰写了专著《高山族舞蹈研究》。可以说,刘先生是台湾从专业角度研究高山族舞蹈文化的第一人。
“应该给民族留一点文化财产”
刘先生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就是运用拉班舞谱重建中国的传统舞蹈、记录中国民族舞蹈特殊动作及其个人的现代舞蹈创作。她说:“我当时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拉班舞谱可不可以写我们民族的东西。比如我们手腕的动作很多,道具很多,枪、剑、水袖很多,后来我就写了几个,写了九支舞,觉得可以用。此后,凡是我创作的舞蹈我都用这个舞谱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就等于建立一个新的文本。那这个新的文本就是世界的语言,你可以用它去跟世界沟通。”
对于舞蹈这种转瞬即逝的表演艺术而言,某种程度上其生命只存在于首演时舞者的能量穿过空间、时间,与观众心灵交接撞击出火花的一刹那。而这一刹那也正是舞蹈作品面临死亡的临界点,有如晨光乍现,然后随着幕落而日暮。即使日后重演千万次,也难捕捉回来首演时的激情与舞作的生命力。舞蹈的历史文献,除残存于舞者的“运动感觉”、身体记忆之外,其他由舞作引发的衍生文字(如评论等),由不同文化背景、艺术修养、价值观的人们从不同视野角度所作的理解诠释,其实都是舞蹈作品本体之外的存在。因此,刘先生常常思考如何将运动感觉转化为书写符号,建立完整的舞蹈文本,以保存人体动作文化。
为了这个目标,刘先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专程到德国追随克努斯特(Albrecht Knust)教授,研究实验以拉班舞谱书写中国民族舞蹈的可能性。拉班舞谱由拉班(1879-1958年)所发明,1928年发表于德国。这个舞谱可以书写人体动作之时间、空间、力度及重心移动,舞者与舞者之关系,舞者与道具之关系,并且可以提供研究者及重建者最详实之资料。以拉班动作舞谱作为舞蹈文本的书写工具,有如音乐五线谱之于音乐的关系,意义重大。
刘先生专业学习拉班舞谱后,依据中国中古世纪和中世纪文献中的文字舞谱及图像舞谱,重建了618-1644年间的音乐和舞蹈,包括唐朝的乐舞、儒家舞蹈以及韩国方儒家舞蹈所作的宗庙舞蹈,同时,也录影记录整部舞蹈作品。
建立中国传统舞蹈文本——这种可书写、可供阅读、可供研究分析、更可供重建再现于舞台上的舞蹈记录,涵盖创作、演出、社会反映,能为舞蹈建立历史存证文本、建设舞蹈文献档案。而这些,在我看来,对于舞蹈文化的传承和保存来说,其价值相当于舞蹈文化领域的《四库全书》。
“我很荣幸,也非常骄傲。由于我生长在一个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孕育了我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研究能力。”从刘先生的创作灵感和创作主旨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她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化的血脉,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也给予她丰富的滋养。她的舞蹈交响诗作品《大漠孤烟直》,灵感就来自唐朝诗人王维的诗作,舞台设计构想则来自科学家及文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刘先生的高妙之处在于,通过舞蹈的身体和相关的舞台、美术、道具、服装、音乐等将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演绎出来,以身体舞动的方式、以舞美造物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与观众分享。
从平面到立体,再从立体的舞台舞蹈转化记录为平面的纸质的舞蹈文献,刘先生完成了一项许多舞蹈人想都不敢想的巨大工程。她的研究和探索,既把我们带到古代中国舞蹈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又让我们回到现实的、民间的、民族的遗产传承中。因此,刘先生也从一个个体的学人变成为文化的引领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家不再仅仅是私人化的生活空间,从家到图书馆的功能转化完成了其主人的社会文化担当。
花莲·“三篇野菜的故事,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变成了这辈子的一个事业”——原舞者执行长吴雪月
我能结识台湾省的本土舞者和学人,是一种深厚的缘分。这要感谢邹人文化领袖、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蒲忠诚先生的引荐和周到安排。
从台北到花莲的太鲁阁号快车沿着台湾岛东海岸南下,西有中央山脉,东有太平洋海岸,山林茂密,海洋无际,果园稻田,一路美不胜收。受蒲先生之托,东华大学的杨政贤教授把我们带到原舞者驻地花莲县寿丰乡。
原舞者:回到原乡,倾听自然和祖先的召唤
原舞者的前身,是1990年在高雄市草衙山胞会馆诞生的“原舞群”。我以前并没有看过原舞者的演出,但据说这是具有国际水平的舞蹈团。本以为这样的舞蹈团应该有很大很像样的办公、排练演出等场地,但映入我眼帘的却只有两栋小小的房屋,排练厅也过于简陋。
为何称之为原舞者?这样的舞团在台湾是如何产生的?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能排演什么样的作品?对我们专业舞蹈院校有哪些借鉴和启发?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与今昔两位理事长以及驻地团员之间的访谈徐徐进行。
原舞者是由台湾高山族精英组成的团体,故此每位舞者也可称之为“原舞者”。初期有33名团员,除副团长之外,没有一个是真正学舞蹈出身的。现在,驻地团员只有10位。我们见到了其中的4位,包括最早的舞者,坚持到今天的元老级舞者,还有艺术总监怀邵·法努斯(阿美人)。后者高大魁梧,双目有神,眼窝深陷,颧骨突起,看起来有点年纪了,但仍有少数族裔特有的英俊帅气,进原舞者团已有22年。他对我解释说:“原”字意涵溯本追源、薪火相传,其使命是研习、采撷、推广族群文化特质及人文风貌。
“来自高山云岭的呼吸,来自大海潮汐的脉动,孕育美丽岛上高山族的舞脉,展现台湾艺术生命的真容,开创世间人文景观的妙境。原舞者,祖先歌舞的传承;山水篇,台湾美学的天机。”在第一次全岛巡回公演简介中,如此的文字道出了原舞者的魂。原来,“原舞者”饱含文化蕴含,富有美学追求啊!但这样说的人很多,要真正做到何其难哉?更何况这样一个没有常规经费支持的民间舞蹈团。
原舞者现在的执行长吴雪月女士,无疑对舞团当下的经营和生存状况最有发言权。她是7年前受孙大川先生影响来到原舞者的,自嘲是“被孙老师陷害的”。“不过真的,我一辈子都很感激他。”原本做警察教官的吴老师,退休后受孙大川约请写了三篇关于野菜的文章,而被推荐到原舞者做了执行长。从跟舞蹈艺术毫无关联到研究少数族群的植物饮食,从第一年想离开到如今她自己的不舍……是什么留住了她?
由于没有稳定的企业赞助支持,要维持一个舞团的田野作业、新剧目编创、日常排练演出、服装道具以及基本生存,其实非常困难。谈及最难、最艰辛的感受,她说:“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想,该怎样留住剩下的这几个人。我就开始算,明年的经费够不够。很头痛啊,我舍得裁哪一个?”吴女士话语中充满无奈和压力……
尽管艰辛,2013年原舞者排演的新剧目《找路》仍然获得一片叫好。编导是阿美人出身的布拉瑞杨,做过林怀民云门舞集的编导。当时,吴执行长想办法拉来大企业的董事和外国友人观看,都说很好,值得推向国际舞台。“常常我们的演出都是自己人看,不行,我们应该要让更多外边的人来了解。我们这里的高山族只占总人口的2%,我们应该要让那些98%的人来看。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很弱的部分。”吴执行长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只有演出,没有营销和传播,这不单是民营艺术团体的发展困境,也是我们诸多院校团体、国际级大团体发展不力的重要原因。林怀民云门舞集的成功,不仅有传统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内核、现代舞蹈的语言形式,更得益于其整个演出产业的全程经营。
不知道原舞者还能辉煌多久,不知道原舞者何时因为没有经费不再排练演出,但他们追寻的薪火相传、文化守护的信念一定会伴随他们的演出,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他们原本的文化传承路径亦如我们舞蹈文化的田野工作:演出前深入民间山野感受学习,拜当地人为师,并发掘这些歌舞背后的文化意蕴,取得族群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对采集的素材进行系统整理并呈现,与现代表演艺术的理念相结合。这种做法使原舞者团员、观众与当地族人之间产生文化的共鸣。实际上,这就是原舞者的宗旨和回归路径:回到田野,回到自己的原乡。《巡回失落的印记》、《百合恋》、《回梦》、《怀念陆森宝》、《找路》……20年间,原舞者学习传承的足迹遍布整个宝岛。
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博弈:找路
在台湾,类似原舞者这样的民间文化艺术团体大大小小有上千个,如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不仅在台湾家喻户晓,在全世界也有相当影响。这样的舞团以其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经营推广模式,已获得社会主流资源和话语权。刘凤学的新古典舞团也有固定的基金支持和稳定的排练场所,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定期演出,与社会主流、社区形成了资源共享和互惠的联系。类似的还有陈美娥的汉唐古典舞团。这些舞团,都以呈现中华文化审美观、哲学观和艺术为最高宗旨。
但是,类似原舞者这样旨在回到原乡、传承高山族舞蹈文化的舞团,其生存与发展并不乐观。在原舞者简陋的排练场,观看嘟嘟、怀邵·法努司几位驻团演员的排练让我感到,原舞者是真正与祖先共舞的人,但他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趋同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根据台湾学者对阿美人宜湾部落舞蹈现状的调查,老年组参与率达到百分之百,而青少年组的参与率逐次下降,只到百分之五六十。高山族的歌舞大部分只在祭祀期间才练,其他时间不能练。此外,一些部落的歌舞其实不适合搬上室内舞台剧场演出。原因是剧场的条件是时间压缩、焦点集中,让高山族老人在剧场演出十分辛苦。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封闭的演出空间,借助复杂的现代舞台技术,对于传统的族群乐舞传人,不仅远逊于山水之间的时空区域,某种程度上还会束缚其手脚、身体、全部的感觉和情感。在原野间,他们可以与山林对话,与大地共呼吸,而在现代剧场面对的则是现代化的灯光音像,只能与机械相对。机械的形式往往大于真实的人存在,人束缚于机械,灵感全无,心灵的自在受到影响。尤其祭祀性的仪式歌舞,更不能抽离土地和固定的神圣时间而搬到现代剧院演出。高山族的舞蹈文化如何在原乡得到保存和传承?又以何种方式进入现代都市剧场?传承和发展还需要不懈的摸索。
无论路途如何艰辛,我们都要坚持。这次对台湾高山族舞蹈的田野考察,其实也是隔海相望的声援和回应!关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都在“找路”,我们一直在路上……
欣慰的是,原舞者的出现,至少对各族群的年轻人有较大刺激,促使他们重新了解、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花莲县寿丰乡光荣村妈妈教室的组织者叶芬菊说:“母语、舞蹈等都快失传了,但我们要把魂传下来。”她所说的“魂”,就是高山族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原舞者的文化复兴和文化催生力量远远超过通常所说的艺术功能与价值。
台东·南王花环部落卑南人母系家长——高山舞集文化艺术团团长林清美
为了讨教、叩问卑南人的生活习俗、舞蹈文化等,蒲先生安排我们从花莲直接到台东。他的朋友林志清研究员(台东南王部落的卑南人)从台东火车站把我们直接送到林清美老师家。林家院子里,她的老伴正用樟木制作卑南人的腰刀刀鞘。82岁高龄的老人话不多,好像不太会说汉语,但慈悲安详。看我对刀感兴趣,他随即从室内取出一把漂亮的刀给我。卑南人三四月份妇女节的时候要佩戴腰刀,到野地砍柴用,只有妈妈级年龄的人才可以配挂刀,后来就变成礼刀装饰了。这是民族工艺品从实用生产生活工具走向工艺审美的一条通则。林志清说“能做刀的人不多了,都是我的长辈。”
见到林清美老师,有一见如故之感。老人开着车进院,非常利索地停车、锁车,有点部落男性酋长的劲头。年过76岁,她却俨然看不出一点老态,行动干练、幽默开朗、能歌善舞,现在是高山舞集文化艺术团的团长,也是当地卑南人花环部落学校的校长兼族语老师,还是妇女会会长。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阅历丰富有故事的老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家宴上的歌舞
入夜,在林家的家宴上,我有幸更真切地了解到一些卑南人的历史。林清美老师召集来七八位伙伴,边吃边唱卑南民歌。一如其他台湾高山族的歌谣,它们都是绝妙的诗篇,也是质朴的生活颂歌。歌声里,有祖先对于人和事物的体悟,有族人之间相互的关怀,有男女之间的思念,有对于神灵的敬畏,有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唱给我们的欢迎歌尤其质朴,情感真挚:“我们围坐在一起欢聚的场面非常美,我们相聚在一起非常美,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你的家乡在北京啊,我的家乡在南王屯,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着我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
不知不觉,我们沉浸在卑南人的歌舞之中。男女依序拉着满溢张力的手,两脚有力地交互蹲跳,上半身扎实不动,结束时有一种身体达到极致的感觉。或欢愉,或悲情;插秧割稻,种小米……歌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阐释的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书写音乐传奇的卑南音乐家
与林清美老师等人的交谈中,他们不断提到一个人,每当说起这个人他们都洋溢着自豪和夸耀的神情。这个人,就是颇受卑南人爱戴的文化音乐人陆森宝。巴力哇歌斯是陆森宝的真名。“巴力”是风,“哇歌斯”是旋风。他从传统中走出,又融入到传统中去,曾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旋律和情感都源自古老的民谣,诸如《美丽的稻穗》、《祭诵祖先》、《兰屿之恋》、《怀念年祭》、《俊美的普悠玛青年》等。
“我工作的地点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我没办法经常回家探望父母与亲友。
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与家人相聚时那种温馨的日子,我的母亲给我新编了花环戴在头上,盛装参加舞蹈盛会。”
这是陆森宝先生的遗作,好多人都会唱。1988年3月24日,他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这首歌,两天后安详地走完人生旅程,享年79岁。这位卑南民谣之父,遗作竟是提醒村子里外出的年轻人不要忘记故乡的年祭,不要忘记年祭大家才能在一起的珍贵时光。对于当下的社会和高山族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老人临终的文化嘱托。
屏东·“脱鞋子的好茶部落”——住在鲁凯人妈妈家
坐火车从台东横穿中央山脉,由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屏东高山族文化园区。天赐良机,听说在屏东县雾台乡新好茶村(当地人称之为“好茶部落”)正好有鲁凯人的婚礼,同时还将举办一个本地文化再生的活动,我们一行赶紧前往。
位于山顶的好茶村,是由鲁凯人和排湾人混居的新村。2009年8月8日莫拉特风灾后,在各方赞助支援下政府主导建设了这个统一规格的新村,现有177户,约300多人居住。在鲁凯人这个传统的婚礼上,盛装的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跳四步舞。动作虽说简单,却让我感受到西方宫廷舞蹈的高贵和盛大。在村子里的短暂停留,最有收获的是偶遇了鲁凯人老师兰美锦和画家卢起村。
“我们小时候好期待过丰年祭”
兰美锦66岁,就住在和我们结对子的鲁凯人接待家庭妈妈家的对面。闲聊中,兰老师给我讲述他们搬迁到这个地方的前后经过。
高山族称好茶村为新好茶,乃原先住地的名称。这是第三次迁徙,第二次迁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从山地乡山地村搬到好茶村,此前还有一次。兰老师的父母都住在旧好茶村,2012年才搬入现在的好茶村。灾民搬进前,援助方已在新房子里备好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煤气灶、热水器、餐桌、床、衣柜等生活必用品,但对于遭遇天灾突然间失去一切的部落居民来说,仍然感觉屋子里空空的,感觉什么都没有了。在旧好茶村时每家每户每口人都有地,可以种地瓜、小米,还可以摘野菜。一些家庭把田荒了,外出打工,由于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开始只能做清洁工等粗活。多数年轻人都到台北的工厂谋生,只留下老人和小朋友。家长有的带小孩到都市读书,原来村子里的学校仅剩下两三个小孩,以致成为空校被废置一旁,老师被迫调走。
兰老师原来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已退休12年。她有一个女儿,在高雄做护工,会讲鲁凯语但不流利。如今,兰老师每周带领村里的老人做健身操、帮他们做午饭,服务长年无依靠的空巢老人,都是义工性质的。我甚至有点心疼兰老师,因为她自己也老了。对此,兰老师显得异常淡定和平静:“没有办法,老人无人管不行,互相照顾吧。”
兰老师除了在村子里做义工,还在常荣百合国小、黎明国小两所学校里义务做鲁凯族语老师,每周三节课,其实只有四五个鲁凯人学生。她自编歌谣、舞蹈、故事,还做服装、玩具等,教鲁凯语的同时也教习鲁凯人的传统文化。她说,孩子们学习族语很困难,如果用歌和舞的方式更容易接受些。
过去,鲁凯人以小米的多寡论贫富。丰年祭总是在小米和南瓜等所有作物收回来之后举行,以村为单位过。兰老师说她小的时候,收获祭要持续两个月,其实这也是休耕的时间。期间,族人都聚在一起,欢欢喜喜地准备酿小米酒,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她家,一边劳作一边歌舞……男人结伴出去打猎、捕鱼的成果,大家也一起分享。
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到新好茶村以后就更不同。兰老师告诉我说,似乎接触到钱就改变了,在旧好茶村一分钱没有生活也很好,也没有乞丐,谁有困难大家都会帮。在家里爷爷奶奶讲故事,感觉十分温馨。眼下,她感觉“民族的文化就要失传了。”丰年祭简化了,祭祀的时间缩短了,祭祀的内容也单调了,甚至对于年轻人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兰老师充满怀念地说:“我们小时候好期待过丰年祭!”
令老人们悲伤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洪水把家里的墓地冲毁,搬迁到新好茶村后,尚没有找到清净之地安顿故去的灵魂。
“你来这里也是用精神安慰我,我觉得明天会更好!”
在接待家庭鲁凯人妈妈家,难得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污染,我们每晚都睡得十分香甜。
清晨早起出门,我先是对住宿的鲁凯人妈妈家的房屋打量了一番。听说这家妈妈的父亲是有名的木雕师,果然房子的外墙及墙沿大多装饰着鲁凯英雄的木雕神像和传统图案。转过身,发现对面人家墙壁上的图画却明显不同。一个画得很大的花瓶插满百合花,一位老妇人用手托护着;旁边,是一位英雄猎人的形象。远远地拍照不能尽兴,我便径直走到对面人家。按照好茶部落的习俗,我脱掉鞋子,进入这家人的院子里,近距离地欣赏墙壁上的画。房子中的主人看到后出来跟我打招呼。这是一位头发和胡须都已经发白的老者。我问墙上的画是谁画的,他说是他的朋友卢起村,就住在村子里。老人欣然应允我的恳请,带我找到了这位画家。
卢起村在墙壁上所画的画,原来都是为了表达对NGO等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他对我说:“你来这里也是用精神安慰我,我会觉得明天会更好!”“你到北京跟人讲台湾有个画家名叫卢起村,个子矮矮的。这就是对我的肯定,我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跟你认识,就等于扩大了我的世界。”画家如此融通开阔的胸怀,让我感佩不已。我说想留一幅他的画作纪念,他允诺中午画一张速写给我。
画家介绍他家对面住着一对勤奋的夫妇,女主人叫瑞珍,拉我过去看看。
这家是鲁凯人的贵族,房子外墙上装饰着百合花的头冠及勇士头像。画家仔细介绍了所画之物的象征意义。百合花在鲁凯文化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贵族勇士头冠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丰富的文化含义,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僭越等级的差别。因此,即使到今天,鲁凯人的房屋装饰和图案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差异。
中午时分,卢画家推着三轮车来到鲁凯族妈妈家对面的人家,架起画架摊开绘画工具,让我坐在椅子上为我画人像速写,他说时间不够,只能画速写,但他骄傲地说他是全台湾画速写最快的人。我听从画家的指导,安静地当起模特儿。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像模像样地做模特儿让人给自己画像。一会儿之后,他就画好了,还题款“难忘的一天”。这幅个人像,是我此次来台湾考察得到的最好礼物。
更让我感动落泪的是,离别之时,卢画家足足用了3分钟时间,郑重地为我们吟诵了祝愿顺利平安的长篇祝祷词。
台湾之行,满眼是别样美丽的风景。当然,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奋力前行的人们,那些台湾高山族舞蹈文化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