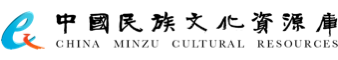
“文明,就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
初春的大漠阴山,白雪仍未褪去。记忆可抵达的700年前,敖伦苏木城还很年轻,有草长莺飞,有铁骑扬尘。唐朝末年,讲着突厥语的西域回纥人东迁,至河套以北的漠南地区定居,由此形成一个强盛的草原部落——汪古部。作为成吉思汗最为信赖的姻亲部落,汪古部参与到元朝的宏图霸业中,并在达茂草原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与这座城齐名的,是嫁给部落首领阿刺兀思长子不颜昔班的三公主阿剌海别。在经历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之后,阿剌海别被成吉思汗封为“监国公主”。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女人和被称为“流失的文明”的神秘“景教”给这个部落带来了时间上的念念不忘。


莲花座上的十字架,出现在1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被盛誉的时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平突厥,经略西域。九年,波斯人阿罗本怀揣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的“聂斯脱里派”教义至长安,被太宗皇帝许其在中土传教,是为“景教”在中国的发端,至唐末在中原衰落。公元11世纪初,景教再次东传,活跃于西北部边疆,居住在今包头、东胜一带的蒙古族克烈部,漠南的汪古部成为它的信徒。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即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这位了不起的女性政治家,以过人的胆识和远见,通过对景教教派的拉拢与包容,为其子奠定了一条开放的宗教政策之路,这使得大元王朝不仅从武功上,更从精神气质上吸引着西方的目光,这位统一中国版图的大汗则以帝王之身与基督徒马可•波罗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而景教也由此在元朝由北向南发展至福建泉州(该地为南方景教中心),历经整个元朝的兴衰。


景教经中亚流转传入中国,与当地文化产生交融与碰撞。在文化的他乡,不速之客该如何融入,如何被接纳,又如何在交往中保持自身的边界,需要时间,更需要策略。在地化或说本土化的方式,成为当然的选择。于是,借助早已取得民间认同的佛教力量,是景教中国化做出的理性实践,莲花与十字架亦即成为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国内留存出土的景教遗物上的基本符号。景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为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说的“土著化”的非土著知识。
眼前此件在内蒙古达茂旗出土的元代鎏金青铜十字架,四面排列有浮雕金刚杵纹,其正面每个金刚杵图案上均有鎏金装饰,十字架上部穿孔则可用于悬挂。金刚杵是藏传佛教里的修行法器,象征力量与智慧;而十字架则是基督教文化的标志,如此混搭,历史便要传递出种种: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高原,金刚杵,象征无畏圆满,十字架,则代表救赎重生,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亦呈现某种文明可能达到的无可比拟之高度。

然而最诡谲的莫过于文化之生命,亦如四季交替、万物轮回,及至元亡明兴,景教也随之消散在东去的长河中。而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在看得见的风景中,被记忆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