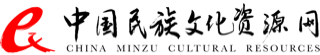草原上的花儿
娜仁其其格的诗,我以前读到时,联想比较多的是她的民族。这个来自东北的蒙古族女子,柔美且具有诗性,显然,她的祖先游走唱歌的血脉在她的身体和诗行里淙淙流淌。
蒙古族作为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游牧民族,生活疆域辽阔,人文历史丰厚,其诗歌及民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娜仁其其格自小受到多重文化的滋养,她满怀深情:
“那蒙古人的长调/马头琴
一个蒙古人的好歌喉/腾格里
你给了我这些的同时/也给了我
一个诗人的灵气与智性/我就是要以蒙古族人的血液
大汉文字来抒写来歌吟——”
她显然是一名具有民族气质的诗人,但她的视野却一路放眼而去,坚持着一种求索开放的姿态。多年前娜仁其其格来到北京,以文学为业,一边当着刊物编辑,为他人做嫁衣,一边写诗,曾参加诗刊社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中国诗歌年选》等,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她在生活的风雨中跋涉,一路劳顿,诗歌是她贴身的家园,我几乎相信,是诗让她有力量前行,走过一程又一程。2010年,娜仁其其格的诗歌经过严格评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这是她多年执着的结果。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诗集,虽然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很久,也很远。早在3年前,《民族文学》就曾推荐她申报过这套丛书,那年参与的诗人实力都很强,众评委经过一番难以取舍的投票之后,娜仁其其格与此擦肩而过。但她仍以她的柔韧等待着。她说她将此作为给自己的一次希望,如同把一颗种子播种在了土壤中,满怀期待地守望,惦记着它是否发芽,是否破出土壤。希望给她这么多年的写作一个交待。
这一次,花儿朝她开放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她这本诗集里,居然果真就有那么多的花儿。写诗本来如赏花,猛然读到让人心动的诗,就如突然闪入眼里的花儿,亮眼得很。而娜仁的诗到处都是花儿:《一朵苦菜花正把生活歌唱》、《梅花印上了她的肩头》、《初冬的牵牛花》、《先于某一年春天的泡桐花》、《大地从此改名叫玉兰 》……,她笔下的花儿各色形态,有的娇美,有的朴拙,有的忍耐,有的灿烂。她似乎是一个种花的女人,将花儿种入了她的诗行,如此喜爱用花的色彩和表情描述人生,传达她的思考。
于是,她的诗含着花儿一般的善意和爱,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无以言说,而她只是以一个女子的眼睛期待着明亮的飞翔,只想用她的声音说着花开,她用《我们说着花开》作为她的标题,说自然与人世的美,而不说花落,但看那红色的翅翼在绿草中闪动,一瓣又一瓣,诗人会爱怜地拾起,又把它们还回草地,“它们在草地中闪着/洁静/喜悦/透彻/多像相爱的人 彼此发现又照亮”。她把诗歌的高贵牵引向对底层的关注,写京城的灰灰菜,与故乡一模一样的灰灰菜,像邻家姐妹,穿着朴素的衣裳;写都市里的向日葵,那些民工兄弟头上的橙色安全帽,就是盛开着的葵花,在她的眼里,带着足可驱散严寒和寂寥的温暖;写胡同口的修鞋妇人,“一双皲裂的手/把一只鞋粘好将鞋掌钉正钉牢”,炎热的夏天过去了,收获的秋天也就快来了。她将诗歌与现实稠密地粘合在一起,让人领略到那些平常屑细的日常情景中的诗意,从而进一步体味到具有普世人文关怀的诗歌所能带来的平和与昂扬,如同扬扬洒洒的微风细雨,给人绵绵细致的滋润。
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里,面对似乎是一片乱纷纷闹哄哄的世象,诗人该说些什么呢?娜仁其其格用她的诗表示:“请原谅 我依然写诗/依然在这个尘世上忙碌与热爱/……就像春天的花朵 来自自然的风和雨/喜欢 这样的明媚与灿烂”。她相信种下一首诗,就是种下了一种人生,就是种下了一种花。她希望因此找到一个能洗掉尘埃、洗掉痛的路口,经过那里,人们能到洞庭湖上去吹箫,引来凤凰,在烟波浩渺中歌舞。海子曾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打动了无数年轻的心,而娜仁其其格有着相似的渴望,要“找到武陵山/进入桃花源/挽起长发/做一个会播种 会插秧/会打腕 会用锄镰的人”,与其说她学了海子,还不如说她以自己的发现为海子作了证明。
娜仁其其格一直在寻找美。她从草原风物的一般描摹中走了出来,在大千世界里寻找诗意,语言素雅,情韵流动,顾盼之间均有美的发现,美的感染,即使有时是含着泪的,带着些忧郁和苦涩,就如她所描画的苦苦菜。但通读下去,会发现那便是一片草原,恰似她的诗名《花儿推着花儿开》,极近缤纷绚丽之美:玉兰、樱花、紫叶李,转而切换成油菜花,软盈盈,亮闪闪,金色的灯盏连成片……让我们睁大双眼,看那草原满地的花儿。